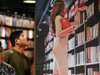想挪用有各種方法
一名曾經在山東某大學做動物研究的人士,聽聞過很多違規使用科研經費的情況。
在最初項目申報時,就需要“過硬”的活動能力,比如,項目申請者對項目審批者“有沒有師生情誼、是否同門,上面有沒有走動,有沒有走關系,有沒有套近乎”,都可能起到決定性作用。
很多科研項目在申請時,設有經費區間,如社科類項目,重點項目經費一般在40-60萬元之間,普通項目的經費一般在10-20萬元。
“一件事情,10萬塊能干成,20萬也能干成,那肯定是往高的申請。”上述研究人士說。
經費指標一般由相關單位研究制定,項目申請時,申請者并不需要自己估算經費,也沒有審查團隊對申請者的項目進行嚴格評估。
只要申請下來,就有各種方法挪用經費。
這位研究人士舉例說,比如要采購一個原來標價60萬的設備,給廠家支付回扣后,45萬能拿到。
武漢一重點大學教授張輝(化名)說,不久前學校發布通知,要求各學院老師自查科研賬務,迎接教育部本月的檢查。他去學校財務處報賬時,看見了有“所謂的”公司,向學校退回科研經費。
他解釋“科研項目的部分工作可以委托給公司,該公司能獲得相關的項目經費。公司經費該用多少,用到哪里,學校是無法審核的。有的教授會將其委托給自己或家屬所開設的公司,合同隨意性較大。”張輝說,最近查得嚴,有人把錢主動退了回來。
根據中國科協2004年公開出版的《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報告》,“全國來說,資金用于項目本身的比例在40%左右”,此前有媒體解讀,這意味著60%的科研經費流失,但中國科協對此予以否認,但其并未明確說明剩余60%的資金去向。
定好了,差的也得買
山東某研究人員向新京報記者表示,事實上,目前財務制度過死,乃至于科研人員的大量時間都浪費在無謂的環節中,比如找發票。“不少人跟我抱怨,很多科研考察的地點都搞不到發票。特別是去野外考察,需要當地人做向導、住宿、甚至打黑車,這些都沒發票。但弄不到發票,就得自己出錢,最后只能想辦法到處找。”
“很多問題都得從體制上找原因。”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所長王毅說。
在經費問題上,管得過嚴、過細,一些大的科研項目上,比如水專項上,“科技主管都快成會計了,反而大家都不愿意做了,項目做得太繁瑣了。”
不僅過嚴過細,而且十分僵化,他表示,“五年前訂的設備,現在降價了,或者不是最好的設備了,但根據規定,還是必須得原價買。”
同樣情況在社科領域也存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一名副教授認為,科研經費管理一方面很嚴格,另一方面又很僵化。有些錢比如勞務費導師不能拿,“但是導師可以聘請助理、咨詢專家。但咨詢費又是可以造假的,比如只給了800,你可以說是8000,財務只管程序,有轉賬單和簽字就行。”
對于社科類科研來說,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顧海兵介紹,搞社科研究的學者,很多時候要和人進行交流和調查,難免請人吃飯、喝茶,但是相關制度規定可以報銷餐費,但不能報銷喝茶費,“這不是很荒唐嗎?本來喝茶更便宜。”
他認為,目前科研經費制度對怎么花錢管得太多,“打醬油的錢不讓你買醋”。
 中國潮人怎么玩游艇
中國潮人怎么玩游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