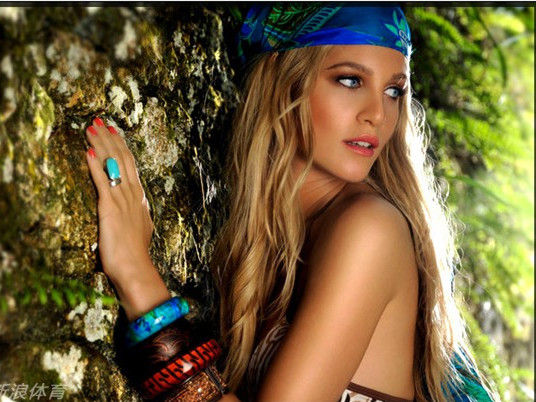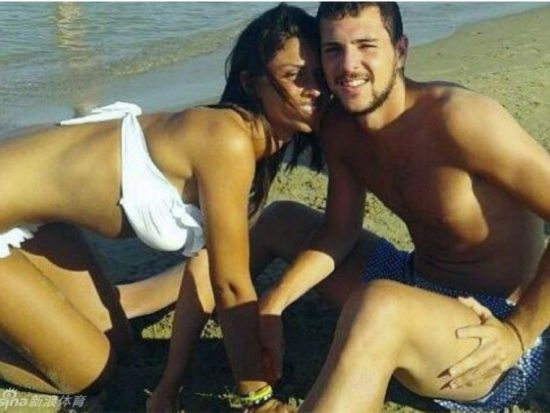論文少,但教課好,高校教師能否評上職稱?近日,煙臺一所高校試行“教學型教授”引發熱議。記者采訪發現,多數高校職稱評審仍按照一個包含論文、課題等的量化指標體系操作,一些高校的青年教師從助教到教授,至少要發20篇核心期刊論文,最多甚至達上百篇。
本報記者 張榕博 尹明亮 實習生 竇梅華 杜貴凱
一線教師講課多,評職稱卻倒數第一
雖然這學期每周要上30節課,對學生也認真負責,但因為沒有一篇發在核心期刊上的論文,這學期期末,省城一家高職院校的青年助教李小琳(化名)在教師評定中仍然評了倒數第一。
日照一家職業技術學院的年輕講師胡靜(化名)說,現行的職稱評審制度其實是一個包含論文、課題等的量化指標體系。
省城一所理工類院校的博士生導師說,在他們學校有這樣一位老師,57歲“高齡”依然是一位大學講師。因為講課能力強,他很受學生歡迎,而且還多次被邀請到全國各大高校去授課。由于忙于上課教學,忽略了科研成果,至今也沒有評上副教授,許多他教過的學生,因為懂得積累評職稱用的學術“指標”,甚至比他“爬得快”。
這位博導說,他1989年從山東大學畢業后應聘為高校講師,到2000年評上副教授,其間在各種期刊、學報累計發表論文10篇,出書三本,11年才晉升了一個職稱。
平均每年要在核心期刊發表兩篇論文
從助理講師到教授,到底需要多少年、多少篇論文和課題?記者采訪多個高校獲悉,高校評職稱,不僅有省里定的標準,還有高校內部確定的標準,甚至還要看領導的喜好,再分批次申報,通過省教育廳確認,標準和時間并不統一。
國內一所211重點高校的行政工作人員說,評職稱需要提供最近三年發表過的論文,在最新的職稱評定公示中,他發現從助教到講師,平均每年至少要有兩篇在國家核心期刊發表過的論文,換句話說,僅這個環節就需要六篇以上論文。從講師到副教授,又是六篇,從副教授再到教授還需要六篇,而且多多益善。如果今年評不上,明年繼續評,那么三年前發表的論文就作廢了。
“由于競爭激烈,一些高校從助教最終晉升到教授,最多要發上百篇。”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說。
“科研成果和授課能力是兩碼事,也是兩個容易沖突的方面吧。”上述博導感慨道。
胡靜則認為,論文中真正的學術含量其實不一定很大。“在我們單位,評職稱看的是論文發表的數量及論文發表期刊的檔次,至于論文在講什么內容,評審時很少有人看,有的高校在評審職稱時,甚至只要求提供論文封面和目錄的復印件。”
通常情況下,論文發表在哪個級別的期刊上,與論文質量有一定的相關性,但在近兩年,論文發表明碼標價,高級別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未必質量高。記者了解到,一兩萬元“購買”一篇核心期刊的論文已是業內的平均價格。
論文多也不保險,還得找評委拉票
至于課題,有教師評價說,評審多看重教師拿到多少課題,而不是課題所取得的學術成果。
上述博導告訴記者,由于學校名額限制,評職稱除了完成論文和課題“硬指標”外,還要人脈廣。“比如今年只有十個教授名額,即使你比往年評上同級職稱的總分高或者發表的科研成果多,也不一定管用,在學校評委投票環節,人脈廣、人緣好的候選人更有優勢。”
胡靜說,如此學術評議的結果就是,促使一些高校教師找關系發表一些科研價值不是很高的論文論著,在職稱評審時再托熟人找評委拉票。
對此,李小琳無奈地說,她很希望學校的評審能來聽聽她上課,但遺憾的是,評職稱很少看課堂教學。胡靜除了每天給學生上課,剩下的精力就都用于寫論文、四處求人發論文。
行政人員“權力”大,反能輕松評教授
曾經憤然表示“永不候選院士”的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原院長饒毅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在評選院士時,有些候選人因為學術以外的原因被“干掉”。“我1995年回國時,參加過中國自然科學基金的一個工作討論,其中就討論到一個科學家的課題,然后我就聽參評的人告訴我,這個人的丈夫剛剛去世,意思是得適當照顧照顧、安慰一下。我說我們討論一個人是不是好的科學家,首先就要去看他的科研成就、教學水平,但現在課題的申報和評審的很多因素與科學無關。”
山東師范大學一位教授表示,在現行“指標論英雄”的職稱評價體系中,一些行政人員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能輕松評上教授,對認真花費大量時間鉆研學術的教師來說是一種不公。
儲朝暉認為,高校教師評職稱拼“指標”和關系,僅是教育行政化的一個縮影,因為一切行政辦教育的結果都是簡單化、指標化對待教育,而專業的學術評價則被淡化。
 中國潮人怎么玩游艇
中國潮人怎么玩游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