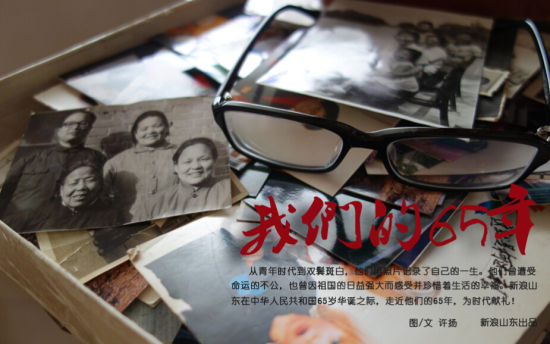8年前,濟南東部草山嶺小區還是片村莊,現在已是高樓林立;3年前,西部的大金莊村民拿到了大金新苑小區的新房鑰匙。從此,這里的居民也有了一個專屬于他們的名字:失地農民。
在外人看來,他們有房:拆遷補的房子;他們有錢:拆遷補償款。但在他們看來,住進了樓房卻又懷念曾經的土地,手里有錢了卻少了安全感。近日,記者走近失地農民這個區別于農民卻又不同于城市居民的群體,聽他們講述內心感受。
從龍奧大廈向南而行,是當地回遷小區錦屏家園,龍洞村失地農民現在的家園。2006年,這里開始拆遷征地,當時村民確實分得了一筆數目不小的錢。村民李斌(化名)回憶,每個人分了三四十萬元,按照一家四口算,能分上百萬元補償款,加上分的房子,不少村民可以說是一夜暴富。然而,手里的錢多了,卻不知道該怎么投資,有的人買豪車,甚至買好幾輛。還有的人放高利貸,但沒想到有人幾十萬的補償款打了水漂。
“放高利貸被騙了,幾十萬元的錢都沒了。”9月下旬的一天,李斌回憶,在他看來,當時拿在手里的錢確實是一筆巨款,都不知道怎么花,存在銀行覺得利息低,想投資希望能“錢生錢”,但又什么都不懂,跟著別人放起了高利貸,沒想到血本無歸。李斌現在已不愿提及這段失敗的經歷。而像李斌一樣大筆的錢因民間借貸而血本無歸的人并不在少數。錢沒了,他們心里郁悶,甚至不愿再外出打工。
小區一名居民告訴記者,現在已經過了投資熱的勁頭,大多數人都采取了保險的做法,寧可把錢存在銀行,即使利息低,也覺得心里踏實。
感受一
不善投資高利貸讓幾十萬的補償款打了水漂
錦屏家園小區的劉如松(化名)今年38歲,他曾將手中的錢購置了挖掘機,但現在已經全都變賣了。“前幾天很多人買機械干工程,起初也挺掙錢,但后來就不行了。”劉如松說,起初分了房子分了錢時,他也想卯足勁踏踏實實干點事。當時有人用錢買了房子,有人用錢買了車,他都沒有動心。“但干著干著就覺得不行了。”劉如松說,干工程很掙錢,但卻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要工程款的時候總是很難。加上很多人都購置了機械干工程,活也變少了,機械閑置的時間越來越多,后來只能變賣了。
他說,有時想創業干點別的,可也沒門路,想干點“體面活”卻又沒學歷沒技能,只能閑在家里。也有買機械干工程成功的,但畢竟都是少數,“想干成點事真沒那么容易。”
創業賠了、勁頭也沒了,小區里不少人思想也變得消極,經常有人湊在一起打牌、打麻將,也不再愿意出去闖蕩。
感受二
也想創業買挖掘機干工程卻難以討要工程款
感受三
內心知足當保安每月1500元也覺得比以前好
感受四
懷念土地沒了土地總覺得心里少了點什么
家住草山嶺小區的王亮(化名)經常站在自家陽臺張望,這里林立的高樓,曾經就是他的村莊。
走進王亮家,有不少花花草草。他說,2006年這里進行舊村改造,蓋起了20棟樓,共有1500余口人,原來的村莊不見了,家家戶戶都住進了高樓,每年還能領到補償款,生活條件好了很多,但他總覺得心里空落落的。“50多歲的人了,現在的主要任務就是看孩子。”王亮說,他的年齡已很難找到合適工作,現在不上班,就照看外孫,總覺得自己年齡不算大,卻不再工作了,覺得很失落。“其實以前村里的地也不多,每家只有幾分地,但覺得心里踏實。”王亮說,現在生活條件好了,但卻沒有了土地,感覺祖祖輩輩依賴的“根”突然就沒了。他說,雖然現在衣食無憂了,但卻很為將來擔憂。失地農民的土地沒了,要是再沒有一技之長,僅僅靠著補償款養老的話,真讓人擔心。
而大金新苑57歲的居民耿勤芝告訴記者,原來住在村里,盡管條件不如住樓房好,但卻自由自在,現在條件確實好了,家里有著200平方米的房子,但卻覺得以后的路不知道該咋走。
9月底一天,北胡村村民楊強康正在值班,他是回遷后小區保安班班長,上班時間為上12小時歇24小時。他說,他很滿足現在的生活。楊強康今年41歲,一家五口人,孩子還在上學,妻子在龍奧做保潔工作。北胡村2014年5月9日正式回遷,村里拆遷補償房子,他有了3套房,一套面積最大的房子他留著和老人一起住,另外兩套120平方米和90平方米的房子他打算裝修一下租出去。
他給記者算了筆賬,現在家里的收入來源總共四塊:村里的補償款,今年每戶每口人分5900元,這是分的第13年了,每年增加100元;他做保安、妻子做保潔每個月能掙3000元左右;租房的收入;過年過節村里發的過節費。“主要收入是干工程,4個月之前還在工地干工程。”楊強康說,去年他在工地上干了8個月,十分辛苦,這也是收入的主要來源。
說起現在的生活,人到中年的楊強康很知足,他說和以前相比,現在的生活舒適多了,人不能不知足,知足才能常樂。
 中國潮人怎么玩游艇
中國潮人怎么玩游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