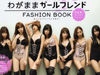《史記》中,只有孔子,以布衣身份而居“世家”之列。
以學傳家,以文化傳世,孔府世家可謂最純粹的文化世家。更難能可貴的是,孔子的文化特質,不僅為孔府世家的世代傳承奠定了獨特的文化基調,還使孔子所開創的文化體系,源源不斷地滋養著中國的傳統文化。
正如被稱為“中國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所說,“孔子以前的中國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國文化又差不多都從孔子那里出來。”
只要愿意,每個時代都能從孔子那里得到精神給養,不過作為家族,孔家的顯赫特權早已被消解,如今的孔氏后人,又如何才能在老祖先的福蔭里重拾“第一家族”的德性光環?
本報深度記者 劉德峰
教儒學要先篩選
2014年9月28日一早,蒙蒙細雨籠罩在曲阜上空。
“人無德不立,國無德不興……”上午9時整,晨鐘九響,整齊洪亮的誦讀聲,伴著細雨響徹孔廟內外,古樸的孔廟被瞬間喚醒。
這是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的曲阜孔廟祭孔大典。當天,由政府工作人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員、海外孔子學院代表、孔子后裔、宗親及專家學者等,組成了4000多人的祭祀隊伍。
而家在曲阜的孔令紹,作為孔子第七十六代孫,卻沒有參加這次祭典。據孔令紹介紹,祭孔活動分為公祭和家祭。“家祭每年就有兩次,分別在春季的清明節和秋季的孔子誕辰日。”
2011年起,孔子后裔聯誼會有意讓兒童加入家祭活動。62歲的孔令紹告訴齊魯晚報記者,這也是家族致力于讓孩子從小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表現,他的孫子第一次隨他參加家祭時,才剛滿3歲。
在孔令紹看來,在家中對孩子培養,是對世家文化的內在傳承,讓孩子接觸祭孔儀式,則是讓他感受世家文化的外在形式。“兩個方面缺一不可,如果只有內在的培養,孩子就感覺不到外在形式所帶給他的震撼了。”
儀式所塑造的神圣感,能不斷強化家族認同。孔令紹仍記得兒時的祭祖傳統,“在我的家庭中,有兩件事幾十年來沒有間斷過。”他說,一個是春節祭祖,另一個則是每年兩次對故去老人的祭拜。
“祭祖臺上擺著祖先牌位,中間是‘始祖至圣先師仲尼之位’,兩側高祖、曾祖、祖父、父母的牌位依次擺放。”孔令紹向齊魯晚報記者描述,半米多高的蠟燭臺、銅質香爐及供果、供菜擺放在供桌上,長輩們坐在祭祖臺前守夜,給孩子們講祖先的故事,講家族的歷史和文化,這些情景都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每次祭典對孔令紹而言也是一次內省的機會。“有如此偉大的祖先,所以不能有愧于祖先和自己,應該比別人做得更好,努力爭取成為一個社會的楷模。”他說。
當然,孔令紹在對子孫內在文化培養方面的用心,絕不輸于在家族禮儀教育方面的重視。孔令紹說,因年齡原因離崗后,生活重心就轉移到了孫子身上。他常給孩子講述孔子的故事,這讓孫子兩歲起就對孔子產生了興趣,提出想學《三字經》。
“為了讓孩子學好《三字經》,我搜集來各種版本,然后從多個版本中各取其長,重新編排。”孔令紹在整理中發現,傳統的《三字經》中“沒有文化方面的代表人物”,于是他填上幾句:“施耐庵,述水滸。吳承恩,云西游。羅貫中,醉三國。曹雪芹,癡紅樓。”
在教孩子其他儒學內容時,孔令紹也進行了類似的篩選。“沒有必要讓他學習全部內容,所以我只挑選了《論語》中關于治學、敬老和修德的50段。”再以《弟子規》為例,他一開始感覺這本書講述的種種規矩,對孩子的自由成長是一種束縛,于是教了兩段就停了。
言傳之外,孔令紹更重視身教。“你教他什么是良好的品德,也得讓他看到怎么踐行良好的品德。”孔令紹說,“要讓孩子看到做人應該守住的底線,守住底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一件事一件事地堅守。”
孔令紹說,行為的影響是直接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比如你在孩子面前堅持不闖紅燈,慢慢地孩子自然也不會去闖紅燈。”孔令紹猶記得,28歲時母親崔昌英去世,彌留之際把孔令紹喊到面前說,“你必須記住兩句話,老實忠厚修子孫,尖酸刻薄損后人。”
“現在回想起那個畫面仍然覺到很震撼,像這樣的教化,終生不忘、代代相傳,對一個人的影響可以說是刻骨銘心的。”孔令紹說。
皇帝親自過問孔家讀書
讓子孫后代接受文化教育,是孔家歷來重視的傳統。“沒有文化的支撐,撐不起世代相傳的世家。”孔令紹說,從記事起,“詩書繼世”四個字就被爺爺寫入春聯,每年必貼于內門之上。
在他童年生活的鄉村,能堅持讓孩子上學的家庭少之又少。孔令紹四歲半喪父,而獨自撐起家庭的母親仍然堅持要孩子上學讀書。
孔令紹一家對家族文化的守護,可謂整個孔府世家文化傳承的縮影。但兩千多年的家族文化傳承,并非一帆風順。
作為孔府世家的開創者,孔子對兒子孔鯉的教育可謂嚴格。據《論語》記載,在孔子不用向弟子授課的時間里,常問及孔鯉學習的進度。“不學《詩》,無以言”和“不學《禮》,無以立”,就是孔鯉兩次經過孔子堂前時,孔子督促他學習并告訴他學習意義的典型寫照。
孔子晚年時,兒子孔鯉和最得意弟子顏回相繼去世,給孔子巨大打擊。此時的孔子,常喟然而嘆,擔心自己的理想和學問無以為繼。幸而嫡孫孔伋察覺到了孔子的憂慮,接過了家學傳承的第一棒。
據《孔叢子·記問》載,“伋于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大意是,父親劈柴,而兒子不幫忙背著,就是不肖,孔伋決定要“子承父業”。
孔伋的志向深得孔子贊賞,孔子著力培養他研習《詩》、《書》、《禮》、《樂》,并不時進行指導。孔子去世后,孔伋又師從曾子、子游及子夏等人,得孔門真傳,并繼續傳予自己的后代。
更為重要的是,孟子曾學于孔伋的學生。因此,孔伋上承孔子、曾子,下啟孟子,在儒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后世尊稱為“述圣”。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孔子的思想以“國家思想”形式得以提升,這也為孔子后人更好地傳承世家文化提供了條件。可至南北朝時期,由于長期戰亂,又導致孔子長孫“子息不昌,文脈不張”,一時再現傳承困境。
即使在文化最不發達的時期,孔氏子孫依然不忘學詩學禮的祖訓。而皇帝對衍圣公的教育也非常重視,光緒皇帝曾當面要孔令貽“延請名師”。
光緒二十年,皇帝問孔令貽“你在家做什么?”孔令貽回答說:“寫字看書。上年奉上諭,命臣延請名師,奈臣家空乏,請不起。”可能是孔令貽故意哭窮,因為下面他接著就向皇帝回報說:“又蒙上諭,查找祀田。臣已咨請兩江總督劉坤一、山東巡撫福潤,并不與臣查找。”皇帝問:“他們為什么不找?”孔令貽回答說:“祀田系湖團地,均在沛縣,此地歸徐州道收糧。不知有何手眼依他們將祀田歸于臣,格外人情并非臣本分。”
即使到民國中期,孔府入不敷出,仍然重視子女的教育,并且緊跟時代,聘請不同學科的老師為子女授課。
孔德成姐弟三人有莊陔蘭、呂金山和王毓華三位長期老師,詹老師和邊老師兩位短期教師,1924年還請吳伯蕭教過一年英語。長期老師中,莊陔蘭進士出身,曾任翰林,應教孔府,不要薪俸,教授經學和書法;呂金山是舉人,王毓華是新式學堂畢業。開設五經四書、七弦琴、數學、英語等課程。
據記載,每天六時半要讀早書,八時與老師共用早餐,餐后有授經、書法、作文、寫詩等功課,十一時下學,回內宅與母親午飯,午飯后繼續受經、學詩、書法,夏日六時晚餐,冬日五時,但晚上要上燈學,每天還要記日記。十天一休,選在“成”日,但很少休息,只有祭祀、掃墓時才放學。
孔子研究院副院長孔祥林說,很多人都批評孔令貽的繼室陶文潽,但她其實是很有見地的女性,兵荒馬亂,經濟拮據,仍聘請名師教授子女多方面的知識,還購置了《圖書集成》等許多書籍。
由于重視教育,衍圣公家族文化素養很高。到了清朝末年,孔府世家子孫中,有著述者已多達三百多人,留下著述近千種。
“上世紀反傳統的傳統該糾正了”
孔家歷代的豐富著述成了今人們家庭教育的源泉,他們常常對比先輩們家庭教育的方式,來反思現代家庭教育的得失。
“比如家書,也是一種教育和學習。”孔令紹說,在傳統的家庭教育模式中,家書是一種一直被重視的方式。孔伋的兒子孔白,也曾云游列國傳播儒家治國理念。彼時,父子兩人常互通家書交流思想。
這一教育方式,被孔令紹重新拾了起來。“在孫子識字之后,每當我有事出門,常會給他留下一封信,上面寫他應該在我不在家的時候學點什么。”他說,遺憾的是沒能長期堅持。
2014年國慶假期期間,孔令紹帶孫子逛公園,在回家的路上,孩子突然提起,“爺爺,你得再給我寫信。”這讓他很受觸動,“孩子并不排斥這種交流方法。”他說,于是回到家以后,他馬上又開始給孩子寫信。
孔令紹在這封信中寫到,“你已經能自學了,這很可貴,自己能做成的事情,就不要只想著依靠別人。”孔令紹告訴齊魯晚報記者,他還寫了他們祖孫二人在公園里玩耍的情景,以及回家路上祖孫倆交流的話。“孩子看了也很受感動,他跟我說,你得把這封信給我收藏好。”
對孔令紹而言,這就是他們家風的一個部分。“家風是什么?我認為家風是一個家族凝聚形成并沿襲下來,對其家庭成員有直接影響或心理暗示作用的家庭文化傳統。”
“像家書、家風這樣的教育,都是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教育方式。”孔令紹說,“現在很多家庭只重生,不重育,只重養,不重教。”在他看來,這正是社會轉型期,家長們浮躁心態的一種表現。
國家層面已經開始強調文化傳統的重要性。2014年9月24日,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講話中說,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對待文化傳統,要堅持古為今用、以古鑒今,堅持有鑒別的對待、有揚棄的繼承。
在孔令紹眼中,執政黨如此正面看待孔子和儒學,是對孔子和儒學理性而又成熟的認識,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孔祥林說,在我國歷史上,也沒有任何一個家族能像孔子世家那樣,能受歷代皇朝所恩寵。作為孔子的后代,他們披有圣裔的光環,享有歷代給予的優渥待遇。但也正因此,孔子思想及孔府世家在“五四”及“文革”時期遭受打擊。
孔子研究院院長楊朝明表示,“在對待孔子與我國傳統文化方面,人們的態度形成明顯的兩極,還是近代以來的事情。不少人將中國落后挨打遷怒于‘傳統文化’,強化和放大了人們對傳統文化負面影響的認識。于是,在20世紀的中國形成了一個‘反傳統的傳統’,似乎中華民族要擺脫苦難,就必須摒棄中華文化傳統。”
“這說明一個民族對其文化和歷史認識上的不成熟。”孔令紹說。
2013年11月26日,習近平到孔府和孔子研究院考察后強調,對歷史文化特別是先人傳承下來的道德規范,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
孔子思想再一次從國家層面受到重視和肯定。由此,如何客觀評價孔子思想及其意義,也成為學界密切關注的問題。
楊朝明認為,封建帝制時期,儒學與政治的結合,使之變得“缺乏平等意識和自由理念”。而與此同時,儒家的核心價值觀念依然深入人心。“孔子學說儒家思想中的積極作用不可低估。”楊朝明說,應該關注具有自由、民主、平等和德性精神的原始儒學,對儒學傳統要有批判地加以繼承,應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
(原標題:第一家族的“自留地”)
 中國潮人怎么玩游艇
中國潮人怎么玩游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