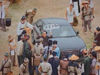文物古跡是一個城市發展的印記,如何處理好城市發展與文物保護的關系,一直是城建面臨的難題。在成武縣古城棚改片區,連綿不斷的廢墟上巋然屹立著成武縣衙遺址、清代呂氏民居、民國時期國民女子中學、文革時期的紅旗劇院等具有歷史意義的古建筑,既延續了歷史留住了鄉愁,也為五平方公里的北部新城留下了顯著的歷史文化符號。這一切,離不開縣委縣政府和有關職能部門的大力支持,縣文物管理所所長郭立和同事們付出的心血、所做的不懈努力也不可小覷。對此,省文物局有關領導欣慰地說:“這才是基層文物工作者應該做的事,非常有特點,在全國都不多見。”
奔走呼吁,為讓古建筑屹立在廢墟上
昨日上午,在位于成武縣紅旗劇院內的文物管理所,牡丹晚報全媒體記者見到所長郭立時,他正在整理保護古建筑的相關資料,準備上報省文物局。“省文物局想把我們的做法在全省推廣。”他告訴記者,并報以憨厚一笑。
據了解,成武3000年前為古郜國國都,如今有省級文物遺址9處、市級17處、縣級34處,館藏文物10236件(套)。早在2013年,古城片區棚改初期,為保護郜國古都遺址和古建筑,郭立就四處奔走呼吁。棚改因為資金問題而擱置后,他沒敢松懈,于2014年10月申報成武縣衙遺址和紅旗劇院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獲批復。2015年6月,呂氏民居也被公布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
2016年下半年,二期棚改啟動,郭立又馬不停蹄地開始奔走。今年3月,他先找到拆遷指揮部指揮長,請求保護文物;又找到新上任的縣委書記崔學民,征得同意。“崔書記是內行,也很重視,上任第三天就去成武縣衙遺址等地查看;到成武就職的第一個周六,就來到文管所,參觀博物館,看碑刻,并就保護古建筑進行深入交流,言談中流露著對我們文物工作者的關懷,讓我特別感動。”郭立激動地回憶道,“從來到走,他和我握了6次手。那一刻,我就默默地告訴自己:可以甩開膀子好好干了!”
“在此后召開的全縣棚改拆遷會議上,崔書記要求,古城街歷史建筑即便現在得不到修復,也一定要保存現狀,不能再破壞。”縣文體局黨組成員申成新告訴牡丹晚報全媒體記者,在棚戶區改造中,為完好保留這些古建筑,成武縣專門成立了由文化部門、公安機關和下屬單位組成的文物保護小組,24小時在現場值班,以防老建筑被誤傷。
很快,縣委副書記韓耀輝帶領文化局、拆遷指揮部相關負責人趕到成武縣衙遺址等古建筑巡視,落實到每間房每棵樹,并安排負責拆遷的工頭。與此同時,郭立和同事為計劃保護的每一處古建筑都上了牌,如同給古建筑擎起了保護傘。
而今,古城片區棚改拆遷工作已經結束,成武縣衙遺址、許氏民居、成武縣國民女子中學、呂氏民居巋然留存。也直到此時,郭立懸著的一顆心才放了下來。“我每次去感覺都不一樣:拆遷前,忐忑不安;拆遷中,憂心忡忡;拆遷后,如釋重負。”他欣慰地說,“未來,我縣將打造五平方公里北部新城。在規劃設計中,新石器時代的古跡大臺小臺、漢代以前的環城大堤、元代的文廟欞星門、清代的老縣衙和呂氏民居、民國時期的女子中學、文革時期的紅旗劇院等古老建筑將修繕復原。這些古建筑不僅為北部新城建設增加了歷史厚重感,也為我縣群眾留住了時代的記憶。這也應和了習總書記所說的‘記得住鄉愁,留得住記憶’啊!”
撿拾的民俗文物,夠建一個博物館了
為給下一代留下寶貴記憶,在保護古建筑的同時,郭立還把“為了將來,收藏現在”確定為自己和同事的奮斗目標。
成武縣文管所不僅有上世紀70年代的小學語文課本、簡報、帶有毛主席語錄的《歷史研究》等文革時期的資料文件、《成武縣供銷志》年鑒、《中國共產黨山東省成武縣組織史資料》(1927-1987年)、最高指示等一批較有價值的書籍報刊資料等,還有青磚青瓦、古舊農具、廚具,酒具、茶具、學習教學用具,生產工具,各種票據和畢業證、煤球證、自行車證等證件,上世紀80年代的書畫、草編、條編、服飾等,琳瑯滿目。
原來,這些都是郭立和同事們今年春天從棚改區挨家挨戶撿來的。“這都是一個時期的產物,是寶貝!雖沒仔細統計,但足有兩三千件,夠建一個民俗博物館的。”郭立自豪地說,“人家都說我們是拾破爛的,不過,別人拾的是以換錢為目的,我們拾的是他們不要的,也是以后花錢買不到的。當時,我們每天都能拾一二百件,雖然很累,但很有成就感。了解我們的初衷后,有的人主動邀請我們登門,看是否有需要的,讓隨意挑揀。”
“在每天巡查中,郭立都不忘搜集文物。我們都說,他有一雙 ‘賊眼’,還有一對 ‘順風耳’。”申成新說,“在我印象中,他就是個機器人,不管什么時間地點,隨叫隨到,雷厲風行。”
市考古所所長孫明則點著郭立的腦袋說:“就你小子能辦出這事,基層文管所如果都像你們這樣,工作就做到家了!”
郭立憨厚地笑了,從一堆碑刻后拉出一個古舊農具,非常認真地說:“這是我在城邊村淘來的,叫砘子,與現在的造型完全不同,從沒見過。當時,我真是如獲至寶,因為它填補了成武縣博物館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