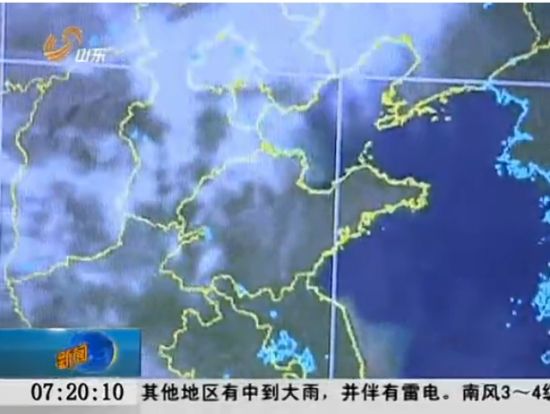南都記者 王星 發自北京
7月1日,北京連續第四天重度污染。11時許,一架從臺北飛來的航班沖破灰霾準時降落首都機場,乘客之一是臺灣歌手蕭敬騰。幾乎同時,北京氣象局發布消息,午后到晚間會有大雨。之后首都機場大面積延誤,當天275個航班被迫取消。
機場37公里外的北京南站沒受到大雨的影響,高鐵、動車基本都準點運行。7月1日剛好是寧杭甬高鐵開通運營的日子,北京到杭州的時間縮短到了5小時2分鐘。
北京南站幾米外的李浩然也慶幸自己沒有淋雨,南站旁高高的引橋雖然不能遮風,但可以擋雨,為無家可歸的訪民們提供簡陋的庇護。李浩然就是一個小訪民,8歲的小訪民。他沒去過首都機場,不知道蕭敬騰,雖然陪爸爸上訪這4年很多時候都露宿在南站橋下,但他沒進過站。這天這個城市熱議的新聞大多數時候都跟他沒關系,除了國家信訪局全面開放網上投訴這條。信訪局希望能引導上訪的民眾更多通過網絡反映訴求,但李浩然和爸爸都不會上網。
對于李浩然來說這天很簡單:白天,跟爸爸在香山攔領導的車,車沒攔到,人被帶進了派出所。晚上,和爸爸睡在南站橋下,要早點睡,第二天早上還要去新發地撿菜葉。
上訪,乞討,磕頭,撿菜,露宿,這就是8歲兒童李浩然的北京生活,到今年7月,這樣的生活剛好過了4年。其間有3個月是在“黑監獄”里度過的。
上訪起因4年前的縱火案
李浩然上個月剛過了8歲生日,雖然沒有蠟燭和生日蛋糕,但爸爸給他買了小點心。沒人祝他生日快樂。當年曾經一起玩過的小伙伴們都在上小學,而他過去4年都在跟著爸爸上訪。
爸爸名叫李德寶,今年45歲,河南鞏義市康店鎮北游店村人,2005年兒子李浩然出生,8個月后夫妻離婚,孩子跟著爸爸。2009年4月3日,李德寶的家被人縱火燃燒,后鞏義市人民法院、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兩審認定作案的是當時與李德寶同居的滑某,兩人發生矛盾,滑某趁李德寶和孩子都不在家,用汽油燒了李家。導致全屋財物損毀、房屋損壞。滑某犯故意損壞公私財務罪被判3年6個月有期徒刑,并在附帶民事訴訟中被認定應賠償李德寶7萬余元。
而李德寶認為此案并非滑某一人完成,而是與自己有矛盾的同村另一人家主使,依據是現場屋門有被撬被踹痕跡,門鎖損壞,而滑某自己有全屋鑰匙,不需要這么做,也沒有力量踹開門。
2013年5月22日,南都記者來到河南鞏義李德寶家,一切都還保留著當年被燒過的痕跡,屋子沒有翻修,沒有再住人,“保存著現場”。
鞏義市公安局負責人對南都記者表示,刑警大隊成立專案組調查。后來因為李德寶持續上訪,“政法委、紀委、鄭州市公安局、河南省公安廳等都核查過,確實沒有疑點。”該負責人說,李德寶懷疑的同村人根本沒有作案時間,更沒有能量影響幾級公安機關的辦案。
“我親自到他家去看,房子被燒了,確實可憐,但你說要政府給30萬,這怎么可能?政府可以按照政策給一些救助,但你不能說自家房子燒了就是政府的全部責任。”該負責人說。
該負責人提出,已經被認定危房的東屋暫時不動,先把受損不太嚴重的南屋修整加固,住回家里來,逐步解決問題。而李德寶則提出要一步到位解決。
2009年7月,李德寶帶著當時才4歲的李浩然進京上訪。從此,李浩然開始了不一樣的童年。
北京生活 和訪民為伴的童年
沒有人調查過像李浩然這樣在北京上訪的孩子有多少。這些孩子跟著家人來到北京,卻不是旅游探親,他們的父母被稱為訪民,他們是“小訪民”。小訪民們大多不懂父母到底受到了怎樣的冤屈,只是跟著在北京上訪。他們不去長城,不去頤和園,但他們中的很多人不時會去北京市中心。因為去了那里,就會被送往馬家樓和久敬莊接濟服務中心,才能登記,才能完成非正常上訪的流程,并被送回家。
從4歲跟著爸爸上訪,李浩然就是住在永定門長途汽車站門口、永定門橋下、南站附近的橋下等地方。前幾年還能住北京南站地下一層大廳的邊角,后來那里不允許居住后,李浩然就只能住在那些露天的地方,南站的引橋就是他們的屋頂,不能遮風,勉強能擋雨。
北京冬天最冷的時候,李浩然也是跟父親露宿在橋洞,“太冷,我就抱著爸爸,可緊可緊。”偶爾城管會來清掃“垃圾”,而垃圾里可能就有訪民們的用具。李浩然和爸爸吃飯一度是用一個撿來的嬰幼兒奶粉罐,撿些柴火生火煮粥。
李浩然跟著父親在北京南站、木樨園等地方乞討,也會在燒烤攤前要飯。北京南站的多位工作人員都還記得這個經常在地下一層大廳乞討的孩子,他跪在地上,身前鋪著一塊喊冤的布。
下午4點多,他們有時去木樨園要飯,有時李德寶把孩子托付給認識的訪民,自己去新發地撿菜回來做飯吃。吉林訪民何淑文說,很多上訪的都見過這個孩子,大家感慨這么小的孩子也來上訪,還經常幫幫他,有口吃的就給他。
南站旁邊引橋下,李浩然把自己的“灶臺”指給記者看,灶臺距離南站站臺的直線距離不超過5米。一道半透明的屏障墻把訪民聚集的露天宿舍和南站里的高鐵分割成兩個世界。
南站地下一層有很多餐廳,李浩然只在過年時吃過一家餃子館送的餃子。記者問他想吃什么,他說肯德基,南站有好幾個肯德基,他從沒吃過。
北京很大,南站周圍人流涌動,李浩然白天跟著爸爸上訪、乞討,跪在來來往往的路人面前。晚上回到冬冷寒風刺骨、夏熱蚊蟲叮咬的窩棚,聽爸爸和旁邊的訪民交流上訪感受,結束一天。他的童年沒有小伙伴,沒有小朋友,沒有玩具。他接觸最多的都是訪民,各種冤屈、不幸、無奈、絕望。他的樣子曾出現在很多路人的手機相冊里,也出現在訪民的大合影里,今年1月3日,露天過冬的20名上訪者在永定門長途汽車站門口合影,拉著橫幅“給腐敗拜年”,李浩然就站在最前面。
黑監獄90天5歲孩子出來后“瘦得不能看”
在北京流浪乞討上訪辛苦,但比在“黑監獄”里還是好了很多。被關押在“黑監獄”里的3個多月,是李浩然最痛苦的經歷。在李德寶的描述中,那是一個位于北京市南五環的院落,兩畝大小,院子里有幾間平房,前院住著男性訪民,后院住著女性訪民,看守———也就是訪民說的“黑保安”則住在大院門口的屋子里。這里沒有人身自由,老板承接各地政府駐京辦的生意,對訪民一律是半夜車接車送,外界將這樣的地方稱為“黑監獄”。
李德寶說,“黑監獄”的老板叫梁霞。同被梁霞的黑監獄關押過的訪民曾見過梁霞的名片,上面印著:為信訪服務有車接送 安排食宿 條件優雅。南都記者撥打名片上梁霞的兩個手機號碼,結果一個停機,一個接通后對方否認自己認識梁霞。
李德寶說,2010年8月1日午夜,他和李浩然被鞏義市信訪局的工作人員從久敬莊接濟服務中心接出,送到了這個“黑監獄”。而鞏義市信訪局負責接訪工作的副局長則對南都記者堅決否認,表示信訪局與“黑監獄”沒有任何關系,政府不會把訪民關進“黑監獄”,至于梁霞則“很久沒有聯系了”。
“黑監獄”有光,電燈24小時長明。還有面一米五見方的窗戶,“可以看到外面的一片天”。沒有日歷,沒有鐘表,手機進來時就被收走了,不知道日期,不知道時間。“我就看日頭,日頭落了就算一天”,李德寶說。
白天干什么呢?“看天。有窗戶,就看天,都一聲不吭看天。”
在李德寶和李浩然的描述里,這個房間有幾十平米,5張床拼在一起的通鋪,可以睡8個人。有衛生間,訪民們吃喝拉撒都在這個屋子里。李浩然和爸爸是房間里的常駐訪民,其他人少則一兩天多則七八天就被各地接走了。屋子里最少時只住了3個人,最多時住過十幾個人,住不下的就睡地上。但南都記者未能找到同期住在該處的其他訪民證實這一說法。
早飯是饅頭,午飯是面條,晚飯是饅頭。“吃不飽,孩子進去時48斤,出來時只剩下26斤。”李德寶說。訪民何淑文見過李浩然剛從“黑監獄”回到南站時的樣子,“我嚇了一跳,已經瘦得不能看了。”
李浩然是唯一可以隨意到院子里的訪民,因為房間鐵門有空隙,他可以鉆出去,看守們也默許了李浩然在院子里玩。大人們下午有一段放風時間。李德寶曾兩次想趁著放風翻墻逃跑,都被當場制止并毆打。白天放風跑不掉,李德寶就想晚上跑。“我一門心思就想逃跑,孩子也顧不上了,我老感覺自己再不走就要死了”,李德寶說。午夜是“黑保安”拉人和送人的時間,這樣可以避免訪民搞清楚黑監獄的位置。2010年10月底的一天,李德寶就趁這個機會往外跑,被抓住按在地上狠打,而李浩然就在屋里熟睡,完全不知道爸爸曾想拋下他自己跑掉。
第二天,太陽照常升起,一切都好像沒有發生過。其他的訪民會在某一個午夜被帶走,又有新的訪民被送進來,鐵打的黑監獄流水的訪民。5歲的李浩然和爸爸被關在這里九十多天。
維穩官員 鎮上核實后付“黑監獄”1.4萬元
鞏義市康店鎮負責維穩工作的社會事務辦主任王娜莉相信李浩然被關很多天的說法,因為鎮上給了“黑監獄”住宿費。
“當時電話打到鎮上,說李德寶和孩子在他那里住,讓我們給錢。”王娜莉回憶說,“我都不知道對方是誰,他說話很不客氣,‘你們是當地政府吧,趕快拿住宿費,我們就放人’,但他要1萬多塊,我就說是不是太貴了,我們去北京接訪也就住一兩百元的賓館,他說李德寶在他們那里住了好多天。”對方說他們每天的住宿費是150元,住了90多天,索要1.4萬元左右。
“我還想說要的錢太多,對方就說,‘嫌多?嫌多你拿5萬我給他滅掉!’”王娜莉說,鎮上只知道李德寶帶著孩子在北京上訪,不知道他什么時候被誰關進了“黑監獄”。最后,王娜莉報告領導后,康店鎮核實確有此事,只好支付了這筆一萬多元的款項。
2010年11月初的一天深夜,李浩然和李德寶被帶走了,面包車把他們拉到久敬莊救濟中心門口后迅速離開。李德寶說自己當時身體很差,又被餓了一天,躺在地上爬不起來。李浩然哭著跑到南苑路攔住了一輛電動車,對方看了父子倆的情況,留下了50元錢。打車打了20元,出租車師傅只收了10元,李浩然和爸爸回到了他們熟悉的北京南站。
當時南站地下一層還能住人,李德寶說自己躺了幾天,每天都是李浩然去要飯回來給他吃。他們又回到了流浪乞討上訪的日子。李浩然就這樣從5歲到6歲,從6歲到7歲,從7歲到8歲。
浩然心聲 不想上訪想上學
上訪的李浩然其實想上學。2013年1月21日,南都記者第一次見到李浩然,他一直笑嘻嘻地聽爸爸和記者說話,一直到記者問他,你想上學嗎?李浩然就哭了,哭了很久才點頭。
李德寶說,因為家被燒了,所以無家可歸,政府不解決這個問題李浩然就無法上學。而在當地政府看來,孩子不能接受義務教育的主要責任正是在李德寶本人。
“你這輩子已經過了大半,但你孩子還有希望,不管怎么樣,孩子都是無辜的,你要是不讓孩子上學,你就對不起他———我就是這么跟李德寶說的。”鞏義市公安局負責人說。當地有一所美國慈善人士開辦的福利機構,“李德寶提出上學只去這家美國人開的學校,我親自給他聯系,通過民政局、教育局協調好,人家也愿意收,最后美國人聽說浩然不是孤兒,家里有父親,堅決拒收。”該負責人說。對此說法,李德寶表示認同。
王娜莉作為康店鎮信訪穩控工作的負責人,與李德寶打了很多交道,李德寶說房子燒了回來沒有地方住,鎮上出錢讓他住在大橋旅社,每天30元。李德寶要求孩子上學要全日制住宿,王娜莉就協調安排,并經鎮領導同意,讓浩然入讀康店鎮最好的康南小學,周一到周五都在學校,管吃管住,所有費用政府承擔。王娜莉說,李德寶提出自己要上訪,周末也不能管孩子,要委托他人照料,鎮上也同意了,每個月出800元給李德寶信任的人負責周末照顧浩然。李德寶認為別人照顧得不好,王娜莉提出最好就是他留在鞏義照顧孩子,并給他在康南小學旁邊租了房子,李德寶還是拒絕了。王娜莉跟李德寶說:“莊稼耽誤耽誤一季,孩子耽誤耽誤一輩子。”她多次勸李德寶為孩子考慮。
這些李德寶都承認,但堅持自己的問題沒有解決,只能上訪,而孩子又只想跟著爸爸。但對于浩然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在變化。1月21日南都記者問浩然:如果可以選,是跟著爸爸在北京上訪,還是在家里上學?浩然說跟著爸爸,“爸爸是我唯一的親人”。過去幾年里,他們幾乎形影不離。
從今年4月開始,李浩然在康南小學正式上學了,小學一年級,5月22日,南都記者在康南小學看到和同學們開心玩游戲的李浩然,再問他同一個問題,李浩然說,“我想在家”。記者問“你覺得家在哪里?”李浩然說:“學校”。
“你還是想上學?”
“我想上學。我去上學,把我爸關在屋里。”
“你能把爸爸關起來嗎?”
“我偷偷的啊。”李浩然說。
幾天后,李浩然又被爸爸帶到了北京。7月2日中午,李浩然在電話里問南都記者,你能幫我把爸爸的事情解決嗎?如果爸爸的事情解決了,我就能上學了。(因涉及未成年人,李浩然為化名)
 中國潮人怎么玩游艇
中國潮人怎么玩游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