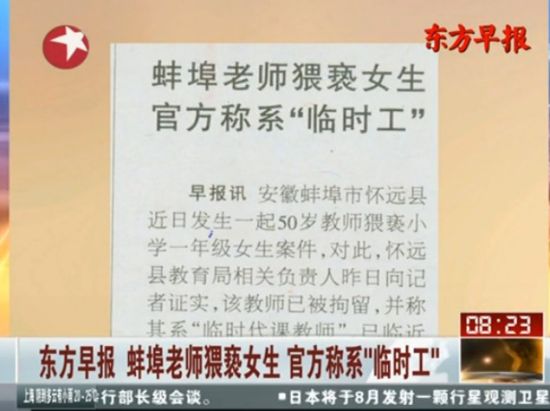“有一個神奇的地方 巴丹吉林把它深深掩藏 胡楊林是天然迷彩 大漠是蜿蜒屏障……”酒泉衛星發射中心主任、山東無棣人崔吉俊這句詩是堅守戈壁綠洲的真實寫照。如今,更多的山東籍官兵從老家一路向西北奔赴航天城,成為山東人里的航天人。從監測、控制逃逸設備,到數據分析,從副總工程師、政委,到參謀甚至普通戰士,神十發射中,這些山東人在不同崗位為任務完成做出各自的保障。
雷測站參謀長: 實時監測火箭飛行
今年是蘇強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的第17個年頭。1997年,19歲的蘇強從復旦大學畢業,做出了一個令周圍人感到吃驚的決定:去山東人當時很少聽說的地方——甘肅酒泉,穿上了一身軍裝。
乘坐火車穿越數百公里沙漠,蘇強才看到了綠色,這就是當時的酒泉衛星發射中心。“來了就來了,學了知識總要找地方試試身手。”這里和蘇強之前的想象有所出入——沒有公路,長途電話只有一部,工作的地方不是在航天城內,而是在距離航天城35公里開外的大樹里:一個沒有圍墻的雷達測量站,一遇大風,滿床都是黃沙。
如今蘇強成為大樹里雷測站參謀長。神舟飛船發射前的500秒時間,監測火箭飛行就是他們最主要的工作,要做到讓整變成零,讓復雜變得條理和簡單。
13日,神舟十號發射前,被稱為航天之眼的大樹里雷測站一片繁忙。30余個監控臺,實時顯示120余組各分系統設備狀態和測量曲線圖。雷達、光學、通信、計算機、氣象和技術勤務保障系統,依次向指揮所匯報情況。
坐鎮指揮的雷測站站長周厚成從容淡定。一條條清晰指令下達,復雜測量跟蹤變得有條不紊。1994年,年僅21歲的周厚成離開聊城老家,來到了這片戈壁灘。
33歲的分管多組雷達設備的雷測站技術二室副主任王健熬紅了眼睛,被戈壁的風沙吹打了11年的他,很久沒有見過同處于發射中心的妻子和3歲女兒。
現任質量辦主管的臨沂人尹勝剛曾是光學設備的室外主操作手。神四發射時,戶外溫度驟降至零下30攝氏度,手握操控盤的尹勝剛緊盯發射目標,平穩清晰的跟蹤畫面獲得了,他的手卻被凍僵在操控盤上。
副總工程師: 加注燃料時呼吸道曾嚴重灼傷
王福通現任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副總工程師,他15歲考入青島科技大學,19歲應征入伍奔赴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為航天事業奮斗了31年。
王福通從小就有當兵的情結,“解放軍叔叔”在他心里是一個無限榮耀的稱呼。因此,當年得到入伍機會后,他立即決定報名。那時,王福通只知道部隊的地點在甘肅酒泉,他在買的地圖上找到了西北茫茫沙漠中的酒泉——這個城市在地圖上只是一個小小的點。
“既然從事了航天事業,我就沒有打算離開這里。”王福通說。就這樣,他在這個高風險的尖端科技領域,迎接著包括神舟飛船在內的一次又一次困難和發射考驗。
說高風險并不為過。1992年,一次燃料加注中,燃料濃度太高,防毒面具對有毒氣體不能完全過濾,王福通和幾名戰友的呼吸道被嚴重灼傷。
“干什么工作都要不怕困難,這在哪個行業都是真理。”
應急逃逸指揮員: 控制逃逸設備 保航天員生命
6月11日下午,神舟十號飛船順利升空,張俊明終于可以松一口氣。作為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發射測試站政委,他已經有三年沒有回過濟南老家。
發射測試站是每一次發射任務發射場系統的最前沿陣地,必須做到一絲不茍、一秒不差。
張俊明介紹,面對“零窗口”發射任務的時候,發射場要把“組織指揮零失誤,設施設備零故障,技術操作零差錯,試驗產品零疑點”的質量目標分解細化到每個崗位、每臺設備。
“山東人的樸實和韌勁都應當用在工作上。”張俊明的話,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許多山東籍官兵身上得到印證。
今年43歲的神十待發段應急逃逸指揮員孫傳飛,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工作了整整21年。1992年,孫傳飛從山東日照來到這片荒涼的戈壁灘,孫傳飛從神舟三號就開始執行待發段的逃逸任務。
如果遇到燃料泄漏、失火、火箭傾倒、控制系統電路失效等各類故障,逃逸時間長的10分鐘,短的只有十幾秒。沒有人比孫傳飛更明白時間就是生命這句話,職務的特殊性讓孫傳飛承擔著巨大的心理壓力。
為了做好航天員的生命保障,孫傳飛和技術部同事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逃逸控制設備。而有了逃逸控制設備,更要在逃逸技術上負全責。
每次任務開始時,孫傳飛要緊盯100多項參數和各項實況圖像,借助電腦進行故障定位、分析和預判。
21年里,孫傳飛成了發射中心的技術骨干,在戈壁灘里也有了自己的家,今年,15歲的兒子要參加中考,孫傳飛卻抽不出時間陪孩子溫習功課。
數據處理室工程師: 分析數據判斷發射是否成功
33歲的臨沂人孟凡昌是發射中心技術部數據處理室的主管工程師,2002年大學畢業后,他只身來到了戈壁沙漠。
十多年里,他把自己沉浸在無邊無際的數據海洋里。
孟凡昌的話不多,但處理的一組組單調數據卻是沙漠里的最強音,因為這些數據將用來判斷發射任務是否成功。
讓數據說話是孟凡昌工作的目標。
除了對火箭、飛船內部的狀態、溫度、氣壓、加電秩序等上千項參數進行遙測外,孟凡昌還需要對雷測站測量的實時數據進行分析和判讀。
研制調整實時數據處理軟件、完善數據庫、調整參數配置等全部準備工作做完,任務尚未執行,孟凡昌和同事已經體會到了任務的緊張強度。
當火箭運抵發射中心的那一刻,孟凡昌的工作就已經開始,把飛船送入太空后,發射使命已經完成,但數據處理工作仍未結束。
最難的工作在發射前,而最累的工作卻在發射后。
發射任務完成后,孟凡昌面臨著5分鐘內完成所有參數分析判讀,并給出相關報告,在神十任務之前,事后數據處理時間為8個小時。
從8個小時提前到5分鐘內,這對孟凡昌和同事們來說,是個嚴峻挑戰。一次任務結束,往往意味著下一次任務就要開始。
埋頭處理數據十多年,孟凡昌迄今仍是單身。
較為封閉的戈壁灘環境和工作環境,讓不少人都有和孟凡昌同樣的情況。
后勤保障人員: 不干技術也堅守神十崗位
擔任技術部參謀的山東萊陽人梁曉東的工作是讓部門參試人員明白各時間段里的不同職責。
看似簡單,但梁曉東需要制定160多份調度方案。從總體流程到某項雷達方案,從部門人員到參試設備,哪個部門在什么時間該做什么任務、由誰執行、不同時間點需要操作哪種設備,都面面俱到。
他的工作要精確到每一部設備和每一個人。
山東德州人董效然是技術部黨支部副書記,每次任務前,董效然都要嚴把用人關,將能勝任的技術員推上任務崗位。
很多參試人員執行任務期間孩子無人照看,董效然又承擔起照看這些孩子的任務,自己的一對雙胞胎女兒卻又成了需要照顧的人。
戈壁灘里水難喝、樹難長,但擔任雷測站后勤處處長的沈孝彬卻把后勤工作搞得紅紅火火。
雷測站里建起溫室大棚和養殖場,發射中心搞起了社會服務部,沈孝彬一人挑起重擔,讓全站實現自給。
戈壁深處的雷測站成了全軍最有名的菜籃子單位,沈孝彬說,他的愿望是讓全站戰士吃好飯。
衛生隊隊長李亞楠入伍28年,給多少戰士看過病都記不清了。
雖然和在航天城的妻子距離35公里,但兩個人見面的時間要么是一個月,要么是一星期。
張良春是發射測試站勤務營的一名普通戰士,入伍十年的他見了山東老鄉顯得有些激動。
如今的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里,有越來越多的山東籍年輕人,他們來這里追逐自己的航天夢想。
 中國潮人怎么玩游艇
中國潮人怎么玩游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