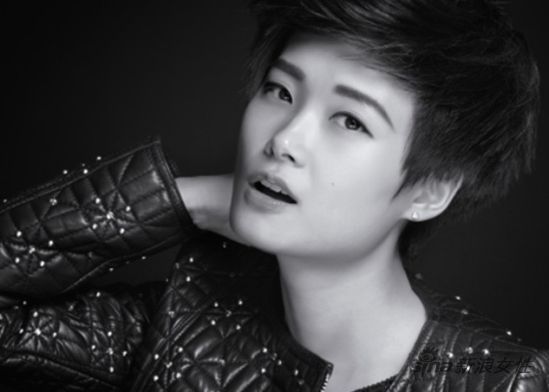劉艾琳
在跑了長達(dá)7年的訴訟馬拉松之后,四川省內(nèi)江市涉及3億元“行社脫鉤遺留債務(wù)”糾紛終于告一段落。
本報記者獲得的一份關(guān)于該市“行社糾紛”案件的內(nèi)部文件顯示,中國農(nóng)業(yè)銀行(2.75,0.03,1.10%)內(nèi)江分行與該市各區(qū)縣農(nóng)村信用聯(lián)社的“行社糾紛”案共33起,總額近3億元。
經(jīng)當(dāng)?shù)卣⑹「咴旱榷喾秸{(diào)解未果后,最高人民法院最終駁回了內(nèi)江各區(qū)縣聯(lián)社立案再審的申請。至此,內(nèi)江各區(qū)縣聯(lián)社最終敗訴,涉及資金2.6億元,部分聯(lián)社已進(jìn)入執(zhí)行期。
其實,在全國各地行設(shè)脫鉤糾紛的持久戰(zhàn)中,7年并不算長。如鄂州農(nóng)信社與農(nóng)行鄂州分行的脫鉤糾紛,已經(jīng)糾纏了17年。
1996年農(nóng)村金融體制改革,農(nóng)行與農(nóng)信社脫離行政隸屬關(guān)系。脫鉤過程中,涉及到大量繁瑣的人、財、資金關(guān)系的剝離,這些巨額且復(fù)雜的債權(quán)債務(wù)關(guān)系并未得到良好的解決。漫長的訴訟之路就此開始。而且,最高院對于行社糾紛的處理方案不斷更迭,一度曾經(jīng)中止,不同時期出臺的解釋辦法也不盡相同。
難以負(fù)擔(dān)的利息
曠日持久的訴訟戰(zhàn),導(dǎo)致糾紛資金的利息成幾何式增長。據(jù)本報初步統(tǒng)計,數(shù)年訴訟下來,敗訴方需要支付的利息往往為本金的3倍左右。
“再審申請被駁回,意味著內(nèi)江市涉及糾紛的信用聯(lián)社都相繼進(jìn)入執(zhí)行期。包袱相當(dāng)沉重。”省聯(lián)社一位高層人士對記者透露。目前,農(nóng)行內(nèi)江分行已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強制執(zhí)行相關(guān)聯(lián)社敗訴所涉資金。
以涉案數(shù)量最多的內(nèi)江某區(qū)聯(lián)社為例,該區(qū)聯(lián)社在執(zhí)行期內(nèi)需要支付農(nóng)行本息共計2682萬元,其中包括本金803萬元,被執(zhí)行的利息是本金的2.5倍。據(jù)上述人士介紹,該區(qū)聯(lián)社本身經(jīng)營較為困難,若被強制執(zhí)行訴訟本息,將給其資產(chǎn)質(zhì)量和員工穩(wěn)定帶來巨大負(fù)面影響。
“我們做過很多溝通和努力,但很難解決。另外,區(qū)縣聯(lián)社作為獨立法人,自身的抗風(fēng)險能力較弱。農(nóng)信社獨特的兩級法人體制,使我們很難像其他商業(yè)銀行那樣統(tǒng)一調(diào)配總分行資金控制風(fēng)險。”上述人士坦言。
高于本金2.5倍的利息,農(nóng)信社方面感覺執(zhí)行壓力較大。同時,農(nóng)信社仍希望能在省聯(lián)社幫助下繼續(xù)追償糾紛涉及的債權(quán)。但情況不容樂觀。四川省金融辦明確提出,對于已進(jìn)入審理階段的案件,政府不宜干預(yù)。
數(shù)份判決書顯示,內(nèi)江市行社糾紛主要涉及農(nóng)行對農(nóng)信社指令貸款、同業(yè)拆借、集資劃轉(zhuǎn)不良以及債務(wù)是否計入利息等矛盾。
例如,其中一宗案件是,1983-1994年,上述涉案數(shù)量最多的信用社(現(xiàn)聯(lián)合社前身)接受了內(nèi)江農(nóng)行的指令,或直接接受借款人申請,或作貸前調(diào)查,或直接以批條貸款的方式,向當(dāng)?shù)亓追蕪S、供銷社、花茶廠等企業(yè)發(fā)放貸款160萬元,至今未收回。同時,還有一筆13.9萬元的同業(yè)拆借資金本息均未能向農(nóng)行收回。
對此,法院一審判決認(rèn)為,農(nóng)行上述行為構(gòu)成侵權(quán),指令貸款和同業(yè)拆借本金損失由農(nóng)行承擔(dān),但利息損失應(yīng)由東興信用社自行承擔(dān)。
雙方均不服提起上訴,焦點在于指令貸款的風(fēng)險是否應(yīng)當(dāng)由農(nóng)信社承擔(dān),及這部分資金是否計算利息。由于當(dāng)初雙方并未明確約定拆借期限和利息,二審依據(jù)人民銀行答復(fù)的逾期同業(yè)拆借計息辦法,判決支持了農(nóng)信社要求償還利息的上訴要求。但指令貸款的利息損失仍判定由農(nóng)信社承擔(dān)。
減少訴累、多元化解決糾紛
行社糾紛案件之繁瑣,牽涉主體之廣,僅從一個地級市的涉案數(shù)量和歷審程序就能看出。而同類的案件還在四川省內(nèi)各市區(qū)、全國各省市不斷上演。
從訴訟主體來看,內(nèi)江各區(qū)縣聯(lián)社起訴農(nóng)行內(nèi)江分行案件25起,農(nóng)行內(nèi)江分行起訴的案件8起。雙方意見分歧極大,案件往往都會進(jìn)行到再審這一層級。據(jù)記者調(diào)查了解,除了四川,吉林、黑龍江、湖北等多省市行社遺留債務(wù)糾紛同樣情況類似。
影響因素來源于多方面。多位參與糾紛的機構(gòu)人士和代理人均認(rèn)為,其中既有金融法治不健全的因素,也有行社脫鉤政策界限不清的原因,更有金融機構(gòu)作為不當(dāng)?shù)挠绊憽?/p>
司法領(lǐng)域?qū)Υ祟惏讣奶幚硪庖娨材砸皇恰?011年初,最高院、國務(wù)院法制辦、財政部、央行、審計署、銀監(jiān)會等機構(gòu)共同出臺了《關(guān)于受理行社脫鉤糾紛案件有關(guān)問題的通知》征求意見稿,希望能形成一個統(tǒng)一的處理意見。遺憾的是,該通知至今未能正式出臺。
中國銀行(2.93,0.02,0.69%)業(yè)協(xié)會維權(quán)部也一直試圖解決行社糾紛的難題。通過全國各省市多起案例研究和參與協(xié)調(diào)工作,該部主任卜祥瑞認(rèn)為,訴訟并非解決行社糾紛的最佳途徑,其不僅會激化行社雙方矛盾,也嚴(yán)重影響雙方利益。
“多元化解決行社脫鉤糾紛是減少訟累、降低銀行業(yè)維權(quán)成本的有效途徑。” 卜祥瑞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他強調(diào),行社糾紛不應(yīng)把注意力都放在訴訟上,應(yīng)當(dāng)大力推進(jìn)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例如協(xié)商、調(diào)解、仲裁等方式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