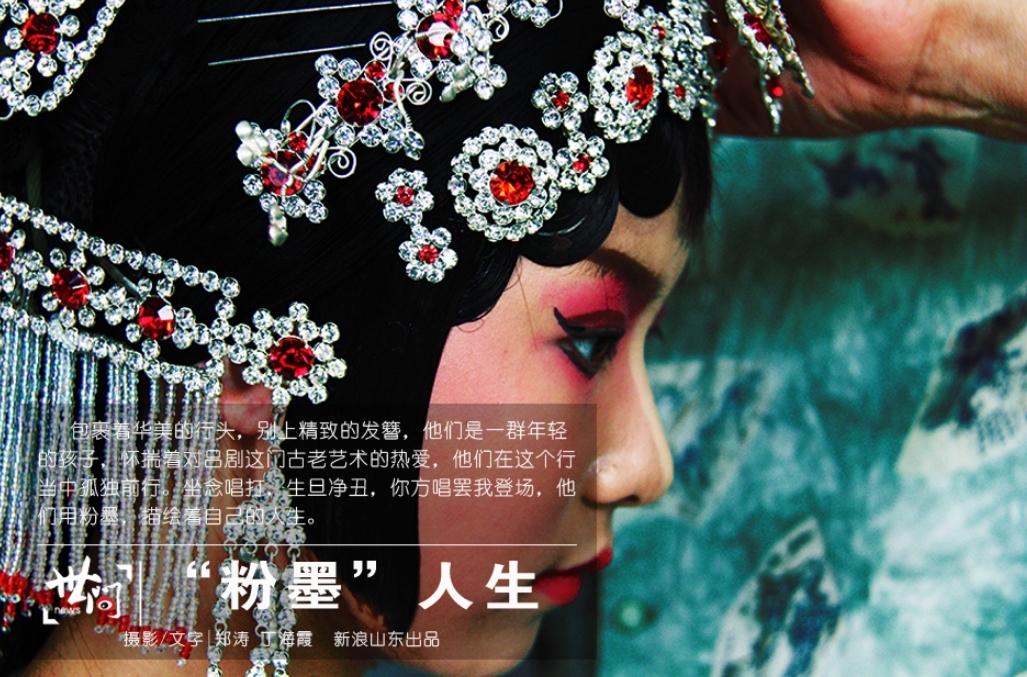原標(biāo)題:女碩士畢業(yè)論文研究下崗母親 看哭答辯老師(圖)
入夏后的一個晚上,48歲的李桂珍像往常一樣騎著電動車下班回家,屋里的桌子上多了個從外地寄來的快遞包裹,里面有本淺黃色封面的冊子。
寄件人是在云南大學(xué)讀書的女兒,包裹里是她剛剛完成的碩士畢業(yè)論文——《母親的故事:一個下崗女工的社會互動和自我建構(gòu)》。
“哎呀,這孩子寫我干嗎?”看到封面上的標(biāo)題,李桂珍在心里嘀咕了一下,但又好奇女兒到底怎么看自己。她飯也不吃了,坐在沙發(fā)上開始翻看,文章很長,里面還有許多“深奧枯燥”的詞,但看著看著,淚水開始漫上來。
李桂珍在云南省西部一個城市的中學(xué)里擔(dān)任宿舍管理員。這個總是窩在角落里拖地、洗校服、刷球鞋的中年女人,曾是當(dāng)?shù)匾患掖笮蛙姽S里的播音員,就連附近鄉(xiāng)鎮(zhèn)的村民都聽過她的聲音。
即使在那個生命中最“輝煌”的階段,廠志里關(guān)于李桂珍的介紹也只有短短12個字:“有播音員1人,每天播音3次”,名字都沒有提起。如今,她只是社會底層一個不起眼的下崗女工,但25歲的女兒花了兩年多時間,用4萬多字,把她寫在自己的畢業(yè)論文里。
母親是一個柔弱的個體,大千世界中一顆毫不起眼的微粒
沿著坑坑洼洼的砂石路,車開進(jìn)一個人煙稀少的山溝,最后停在一塊三角形的空地上。
李桂珍下了車,看上去興致不錯。她指著前方說:“這就是我們工會,那個是舞廳,那個是電影棚,我的廣播室就在電影棚上面。”
順著她手指的方向看過去,只有一片爛泥地和荒蕪的雜草。遠(yuǎn)處是幾排低矮而整齊的紅色磚房,窗戶玻璃支棱著凌厲的尖角,里面黑洞洞的,早已無人居住。可李桂珍和同行的幾個人對著這片廢墟,聊得很起勁。
這一幕讓站在旁邊的女兒蔣易澄感到好奇。當(dāng)時,這個云南大學(xué)傳播學(xué)專業(yè)的研究生正在準(zhǔn)備自己的碩士畢業(yè)論文,她要研究“三線工廠”職工的集體記憶。此次回老家參加父輩們的聚會,是田野調(diào)查的一部分。
蔣易澄是標(biāo)準(zhǔn)的“三線子弟”,她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姨媽舅舅都屬于一個代號叫“國營七礦”的鈾礦冶煉工廠。1970年代,他們響應(yīng)支援三線建設(shè)的號召,從全國各地來到這個距離昆明500多公里的小山溝,把這里逐漸建設(shè)成一個擁有糧店、百貨店、學(xué)校,甚至舞廳和燈光球場的山中“小社會”。
李桂珍和蔣易澄腳下的這塊三角地,曾是整個礦區(qū)的中心。“七礦”最輝煌的時候,接近2000人在此工作、生活。1990年代末,國有企業(yè)改革,“七礦”宣布破產(chǎn),李桂珍買斷工齡下崗,職工接連離開礦山自謀生路。如今,整座工廠只剩下5位老人看守。
雖然成為單位“甩掉的包袱”,但提起“七礦”,李桂珍仍掩飾不住自豪,“原子彈爆炸我們是作了貢獻(xiàn)的!”她總喜歡對外人這么說。此次女兒回老家采訪三線建設(shè)的事,她跑前跑后幫忙聯(lián)系老同事,帶女兒去退休人員安置點,讓那些老人講講“采掘隊大干多少天”的輝煌記憶。
蔣易澄最初并沒有注意到母親有些反常的舉動。對她來說,母親只是自己眾多采訪對象中的一個。但母親在聚會中不同于平時的表現(xiàn),讓她開始好奇,為什么在家里有點敏感、一度不愛與外界接觸的母親,重回“七礦”后那么開心、健談?她在那里到底經(jīng)歷過什么樣的時光,離開礦山后又遭遇過什么打擊?
盡管和母親朝夕相處25年,但這些問題她并不太了解。
回到學(xué)校后,蔣易澄去導(dǎo)師的辦公室里匯報論文進(jìn)展。聊天時,她無意中提到母親下崗后爭取權(quán)益以及出去打工后心理上的變化。坐在對面的導(dǎo)師聽了眼睛一亮:“這反映了人的自我認(rèn)知的發(fā)展。”導(dǎo)師推薦她回去讀讀美國學(xué)者喬治·米德的《心靈、自我與社會》這本書。
“人的心靈和自我完全是社會的產(chǎn)物。”書里有這樣的論斷。
蔣易澄開始重新審視這個最熟悉的采訪對象。“母親是一個柔弱的個體,大千世界中一顆毫不起眼的微粒,但為什么此刻看她竟覺得她如此強(qiáng)大?如果時代洪流總是將人左右,讓人無奈,但人也是可以反抗、適應(yīng)和改變的。”她在論文中寫道。
這個年輕姑娘意識到,自己本來要探尋的“七礦”發(fā)展、變遷歷程,其實早就與母親的命運交織在一起。但蔣易澄并沒有告訴母親,自己論文中的主角已經(jīng)換成了她。





 中國潮人怎么玩游艇
中國潮人怎么玩游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