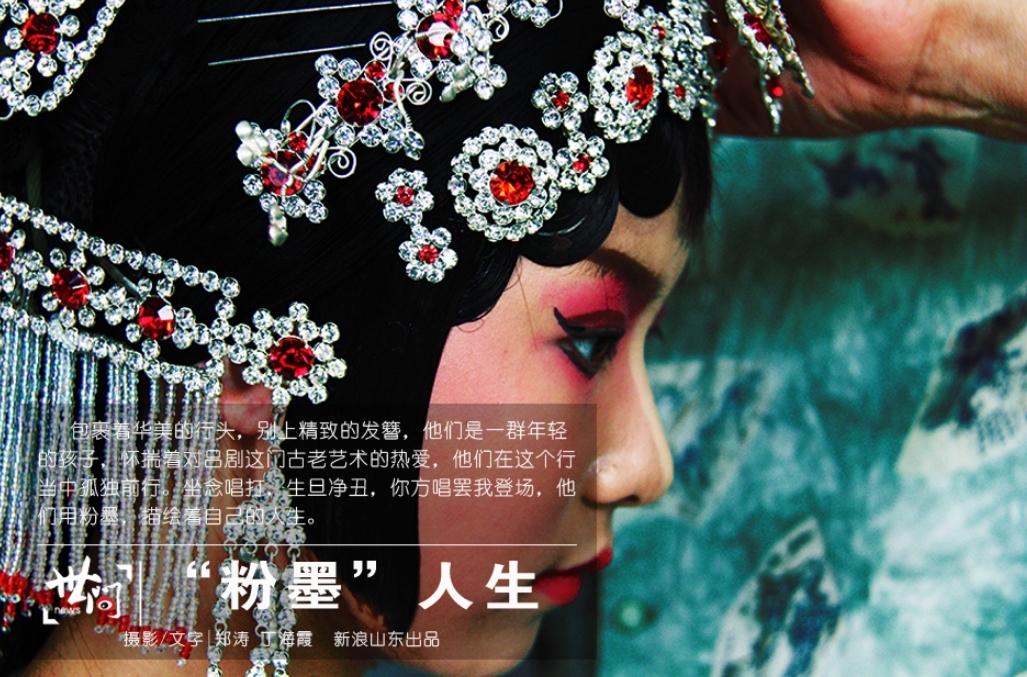有一次,蔣易澄獨自回“七礦”采訪。那天天空下了很大的雨,山中霧氣濃,什么都看不清楚,路上沒什么人,周圍安靜極了,只聽見雨點落在地上的聲音。她坐在小賣鋪門前躲雨,幾只小雞在她腳邊來來回回地啄食。那一刻她突然覺得時間靜止了。
正對著的地方曾經是廣播室和電影棚,母親就在里面播音。“礦廣播室今天的第一次廣播現在開始,下面轉播中央新聞……”喇叭的功率很大,附近鄉鎮都能聽到。等到了晚上,電影棚會放露天電影,人們帶著小凳子和飯菜聚在這里。
如今,她眼前的只有荒草和泥巴。電影棚和廣播室早已夷為平地,廠里曾經最時髦的燈光球場也變成爛水塘。
“突然覺得,原來不管怎樣生活還是要繼續的,要去過自己的生活,有時候確實很無奈,但有些東西你根本改變不了,只能往前走。”這個25歲的姑娘說。
這是這個答辯季看到的最鮮活的論文
得知論文答辯分組后,蔣易澄有些擔心。云南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郭建斌是這一組的答辯老師,他的綽號是“殺手”,上課時很嚴肅。蔣易澄的論文光看標題就顯得有些與眾不同,這畢竟是學術研究,不是文學創作。
“能過嗎?”有人表示擔心。
答辯前一天,蔣易澄的同學突然“炸了鍋”,他們讓蔣易澄趕緊看郭建斌的微博,“你這個肯定沒問題了,老郭都認可你了。”
那條微博寫的是:“一個學生的碩士論文,居然寫的是她的母親……這樣的論文,差點看得掉淚了!這是這個答辯季我看到的最鮮活的論文!”
事實上,郭教授看到論文的開頭時就被吸引了。“我們對我們父輩那段歷史和生活經歷其實不太了解,而且缺乏和父母共同做一些事情的經歷。”論文中蔣易澄幫母親去學校打掃衛生這個不經意的細節讓他很感動。盡管認為論文的理論部分稍有欠缺,但他充分肯定這種“接地氣”的嘗試。
郭建斌試圖在記憶中搜尋這個女孩在自己課堂上的表現,可沒有任何痕跡,她很少發言,一直都很低調。
本想繼續保持低調的蔣易澄現在火了。郭建斌的微博發表后,外校的老師也來索要這篇論文,一位新聞學院的女院長看完后哭了。答辯現場,提到幫母親做衛生那個細節時,郭建斌也有點哽咽。“這是一個懂事的閨女”,他當著所有人的面這樣說。
站在臺上的蔣易澄聽了“好想哭”。“不是因為他表揚我,而是因為有個理解你的人,那一分鐘特別受觸動。”她說。
論文答辯前,蔣易澄把這篇論文快遞給母親,想聽聽她的反饋。李桂珍這才知道,自己成了女兒的研究對象。
“她成熟了很多。”李桂珍說,“平時說不出來的話寫出來了。”
看完論文,接通女兒的電話時,李桂珍已經恢復平靜。她甚至有點挑剔地說:“有些用詞語句還不是那么流暢,很多故事還沒寫進去。”
“哎呀這個是論文,不是你想寫什么就寫什么的。”蔣易澄忍不住笑了。她根本不知道,要求總是那么高的母親在打來電話前剛剛哭過。
蔣易澄的論文也完成了李桂珍一直以來的一個心愿。1998年,蔣易澄的外公被檢查出矽肺晚期。他是一名八級鉗工,當年響應國家號召,帶著全家從貴州到這里支援三線建設。他在病床上跟兒女說:“我把你們帶過來,現在帶不出去了。”
當著父親的面,李桂珍一直忍著,回家后才大哭了一場。那時她下崗,姐姐下崗,哥哥下崗,嫂子也下崗,幾乎全家人都下崗。“如果我們條件好一點,他精神壓力不會這么大,因為他也自責,是他把我們帶進礦里的,他覺得是他的責任。”李桂珍的眼睛濕了。
兩個多月后,老人去世了。臨走前,他曾想買塊手表留給妻子,只需要兩三百塊錢。可拮據的老鉗工沒這筆錢,女兒李桂珍也掏不出來。這個遺憾讓她至今覺得愧對父親。她想把父親的故事寫出來,“我覺得我爸跟王進喜比也不差啊!”
蔣易澄考上新聞學院后,李桂珍叮囑女兒:“你學這個嘛,要在寫作上好好練一下,如果有機會,將來把你外公、把七礦的事寫出來。”
她只是這么一說,但蔣易澄一直記在心里。
 中國潮人怎么玩游艇
中國潮人怎么玩游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