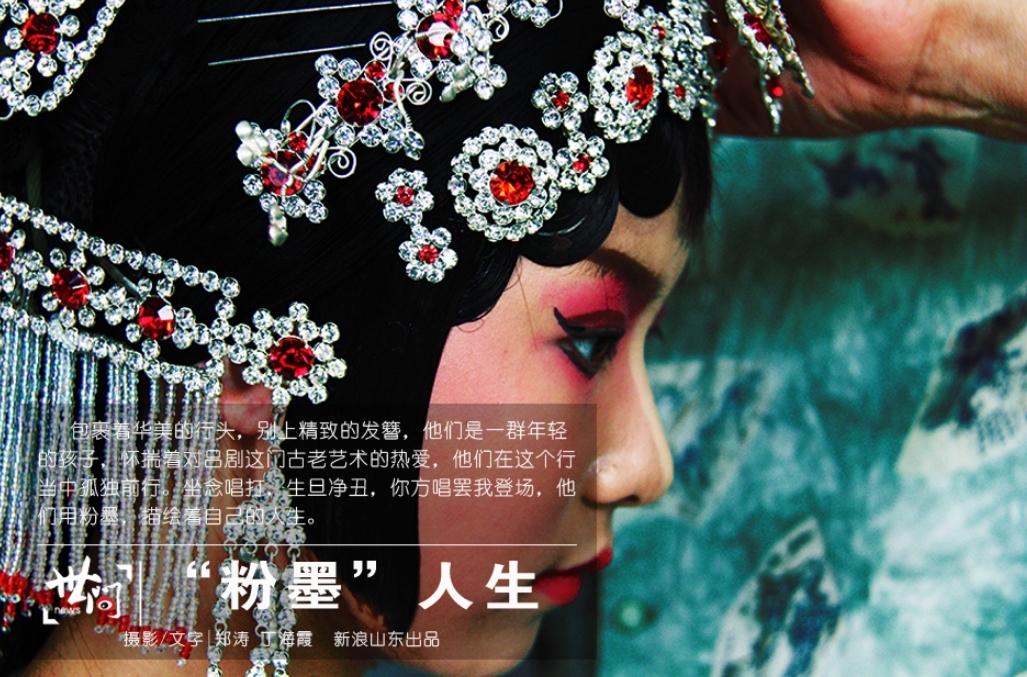第一次再就業的嘗試受挫。“從表面上我這個人很樂觀,但我常跟我女兒說我不敢想,我怕我鉆進去得神經病。”李桂珍說。
一次偶然的機會,聽說當地一所中學有公益崗位面向“4050”人員招聘,當宿舍管理員。她應聘成功,可干了半個月就有點受不了。她在工廠都沒怎么干過體力活兒,如今拖地拖得手直翻筋,膝蓋都不會打彎了。
李桂珍有點打退堂鼓。她回家跟丈夫傾訴,可丈夫聽著聽著忍不住想“吼”她:“咋會一天就是在抱怨!”周末一個人守著空蕩蕩的宿舍樓,她只能打電話跟女兒“吐槽”。
“不要太去計較利益,遵循自己的內心。”在外地讀書的蔣易澄在電話里安慰母親,“做什么都會遇到問題,會有不同的煩惱,現在你這種心態做什么都會煩惱。”她分析著,已經不再是那個在被子后面餓得睡著、需要媽媽照顧的小女孩了。
聽了女兒的建議,李桂珍決定堅持下去,“管他呢,做事情力氣出了還會有,也不會累死,就做唄。”她翻開自己的手掌,幾條凸起的青筋趴在手背上,“我以前細皮嫩肉的,現在老繭都出來了。人一輩子不會一帆風順,我鼓勵我家女兒,你多讀書,現在苦就是為了比父輩母輩過得好嘛。”
母親的期待對于蔣易澄來說更像是一種無形的壓力。“她自己覺得很挫敗,所以會把那種東西轉移到我的身上,要求特別高,想讓你無時不刻地好、好、好。他們怕你吃虧,怕你考慮不周全,我做什么老是覺得受束縛,變得跟他們一樣要考慮很多東西,放不開,很累。”蔣易澄說。
她也曾因此發過脾氣,但現在想明白了。“每每回想起來,才深刻發覺自己很是愧對母親,我從來沒有真正了解過她的需求,不知道她情緒不好的來由,不理解她的擔憂、焦慮和孤寂,太多太多,有時候甚至厭煩她對我過分依賴和給予期望,我不明白人生歷程是這樣地短暫又漫長,不懂得在面臨人生抉擇的時候還有很多復雜的原因和時代背景,也不清楚人到中年沒有固定工作又沒有養老保障的那種失落和焦慮。還好,借由這次畢業論文的機會,讓我提早體會、省悟。”在論文后記中,蔣易澄這樣寫道。
探尋母親的“自我”,也是在不斷拷問自己的“自我”
隨著論文的進展,越來越多的問題超過蔣易澄預想的范圍,探尋母親的“自我”,仿佛也是在不斷拷問她的“自我”。她要跟著母親上班、買菜、勞動、做家務、聚會,有時也會不耐煩。
放假回家時,蔣易澄常去學校幫母親做大掃除。她拖洗走廊地板,擦大廳的玻璃窗,戴上塑膠手套撿草坪上的空瓶子。休息時,母親讓她幫忙出了期黑板報,蔣易澄隨手畫了幾朵向日葵和一個拿著書的小男孩,母親在上面寫了一行字:“歡迎同學們歸校,歡迎新生入住,你們到家了!”
李桂珍已經適應了自己的新工作。她讓女兒上網查如何管理初中宿舍、如何搞好宿舍文化的資料,然后把這些摘抄在筆記本上。蔣易澄翻過那本筆記,里面還有母親之前在床上用品店參加家紡培訓的筆記。她發現母親一直在默默地補充知識。
李桂珍的管理方法很見效。她跟那些總是板著臉的宿舍管理員不一樣,檢查衛生時看到哪個寢室做得不好,她自己動手打掃干凈,然后寫張小紙條放在床上:“帥哥,你們下次就像宿管這樣去做。”她熟悉這棟宿舍樓里每一張臉,坐在一樓管理室的推拉窗后面,她大嗓門提醒那些飛奔的男孩:你的衣領沒翻出來;你的鞋帶開了;站住,你不是這個宿舍的。
男孩子很喜歡這個宿管阿姨,他們把喝完的飲料瓶子堆在教室后面,晚上下自習后帶回來給她。老師說,他們還把李桂珍寫進了作文里,“你是怎么把他們豁住的啊?”
蔣易澄也要把母親寫在自己的文章里,但她要寫的不是一篇幾百字的作文,而是畢業論文。這讓她有點矛盾。
“要不斷把我媽牽涉進來,但是我又不想把她牽涉進來,畢竟要給老師、同學看的,甚至以后上網了,大家都可以去看,感覺會把自己的家庭故事暴露出來,心里面還是有所顧忌。”動筆前,蔣易澄一直給自己做“心理建設”。
“在別人看來,她媽媽只是一個宿管員,拿出來說會不會……但是我很早就對這些東西不在意了。我不會覺得我媽媽下崗在家沒工作,我就丟臉。如果同學問起我媽是干什么的,我就說在家,當家庭主婦。”說這話時旁邊恰好有人經過,她的聲音不自覺地變小了一些,但很快又恢復了自信,“我覺得我媽挺優秀的,不是拿不出手,大學時我媽經常給我織毛衣寄來,別人特別羨慕。”
對于蔣易澄來說,這篇論文不僅僅是一篇文章,“它提供給我太多思考的層次,關于人生,關于婚姻,關于個人的命運,以前特別無知,不會思考這些東西,一下子覺得是個成長儀式。”
 中國潮人怎么玩游艇
中國潮人怎么玩游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