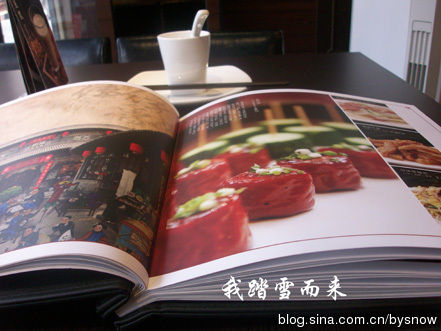閑來問姨媽山東面條怎么個抻法,她說:“面里加點鹽兌點堿,剛開始抻不開,就切成面片,慢慢地就拉長了,”說到這兒,她停頓了一下,想起了什么,若有所思地看著遠方,“你姥爺抻得面條像頭發絲兒那么細,再盤成餅,多少年了,再也沒出一個那樣的人,紅白案都精通啊。”
姥爺的故事偶爾從長輩話語中夾帶過:從山東濟南府闖關東,倍受王爺禮遇,每逢王府有貴賓,王爺差人套兩輛車接姥爺來掌勺;建國后,姥爺的飯莊公私合營,和政府第一把手領一樣的工資……因為姥爺魯菜做得好。問母親當年吃過姥爺做的哪些菜,她說不上來,只是一提這個話頭,她就說:“你姥爺天不亮就要上班了,一年都不歇著啊,天冷了,早起先燙壺酒暖暖身子……”積勞成疾,姥爺過早地離開了,他的外孫女還沒出世呢。
近來對魯菜稍有了解,因為有了像姥爺那樣背井離鄉的山東人,魯菜才在北方扎根,開枝散葉,北方的飲食習慣大都受魯菜的影響。過去人學藝,一招一式非得不短的時日,沒有捷徑可走,更沒有速成法,一朝業成,伴隨終身。
走在濟南的街頭,看著店招上那些熟悉的字眼:單餅、地瓜、大米干飯……我從母親那兒接力了這些叫法。到了濟南,一定要嘗嘗地道的魯菜。魯菜是官府菜,做法講究,費工費料費時,包括孔府菜、歷下菜和福山菜。孔府菜最講究,當年接駕賀壽的,有的菜歷時七天才能燒成;福山菜以煙臺菜為主,主要是海鮮;我這次品嘗的是歷下菜,也是傳統的濟南菜,醬香突出。
九轉大腸:清光緒初年首創。“九轉”出典道家,道家煉丹有“九轉金丹”之說,九轉是精煉久燒之道。吃此佳肴如吃仙丹之美妙。
廚師像道家“九煉金丹”一樣精工細作,下料狠,用料全,五味俱有,制作時一焯、二煮、三炸、四燒,出勺入鍋反復數次,直到燒煨即熟。慢慢品嘗,酸甜苦辣咸的滋味在舌苔上蔓延。直到在火車上靜待回程,九轉大腸的宮商角徵羽五味宛如在舌尖彈奏,余韻無窮。
糖醋鯉魚—濟南北臨黃河,黃河鯉魚肉味純正,肥嫩鮮美。《詩經》亦載:豈食其魚,必河之鯉。黃河之鯉打撈自黃河重鎮—濼口,先經油炸熟,再用著名的濼口老醋加糖制成糖醋汁,澆在魚身。濃而不厚,色澤金黃。鯉魚頭尾翹起,魚身兩側百葉花刀刀口爆張,恰似魚躍龍門。